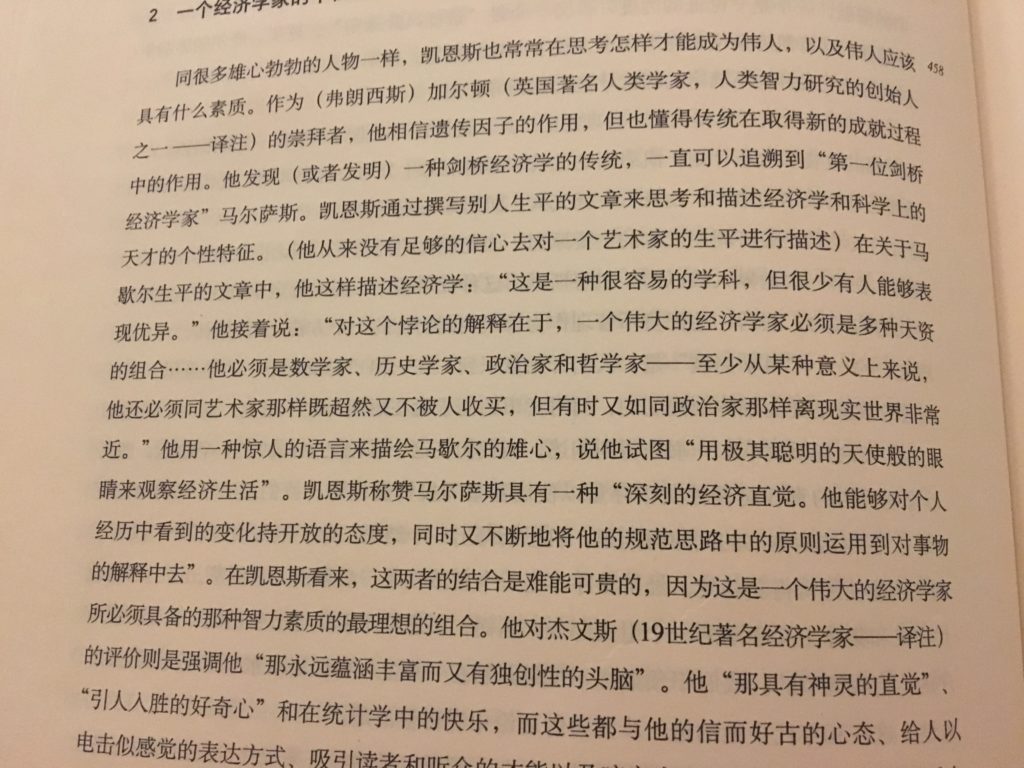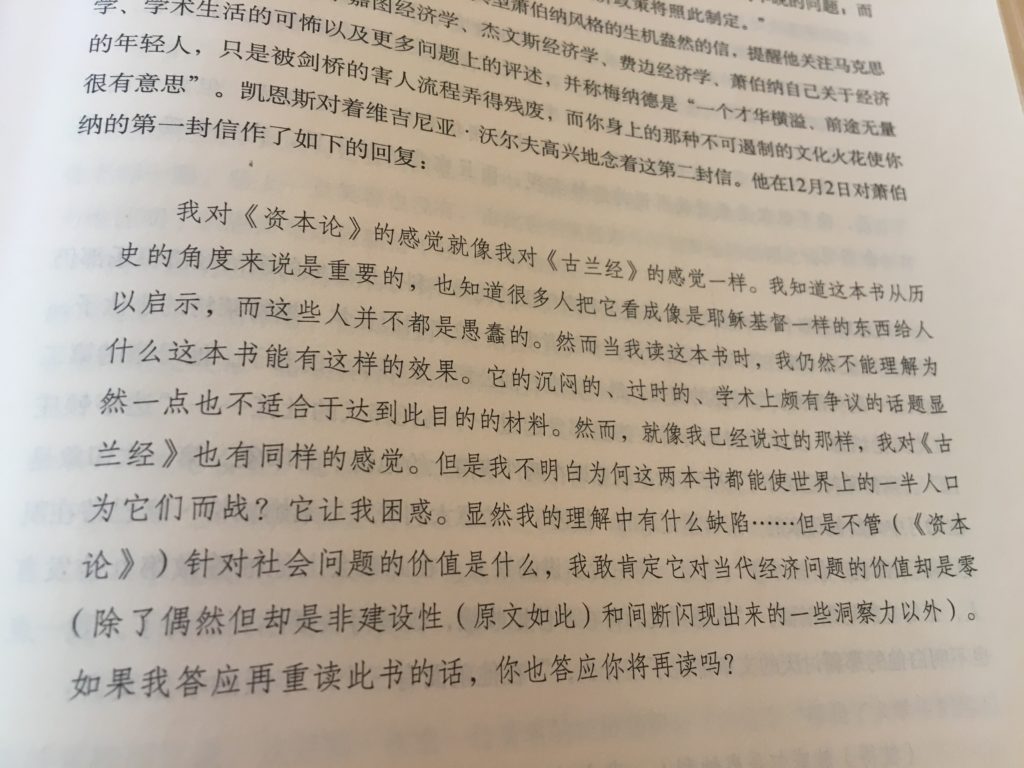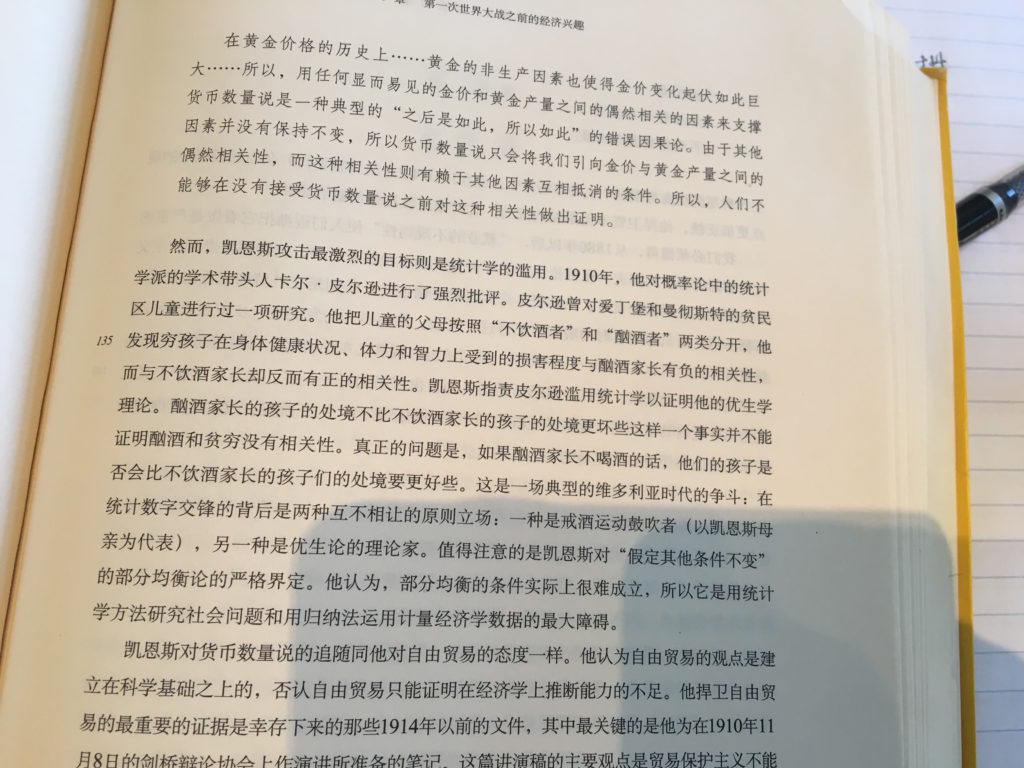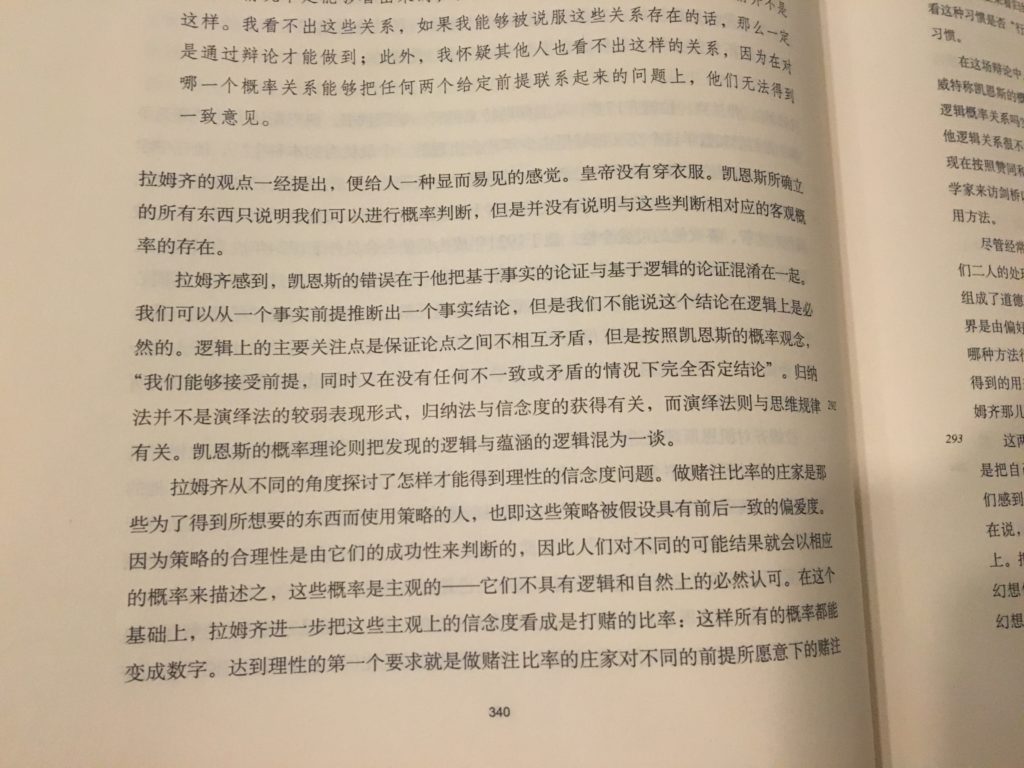昨天读了一大半,剩下了一小半,今天继续。
凯恩斯毕竟还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的。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感慨经济学真的是什么都学,除了经济学原理本身之外,我们还得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法律、数学、统计、计算机,甚至于物理——有些思维总是想通的不是?大概就还跟化学还没啥交集吧,连生物都有交集(一是跟生统和流行病学什么的有交集,二是跟神经经济学有交集)。
学的乱七八糟其实对于人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在西方教育体系下面,其实人文学科是比较难学的。对于理(工)科来说,极度的打磨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是最主要的训练,而对于人文学科则有点考验见海纳百川的功夫——如何把零碎的散落在各个角落里面的东西或紧或松的串联起来。
以前最茫然的就是去艺术博物馆,尤其是当代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大概这几年在欧洲呆过、在上海的时候也全国四处晃荡、到了美国更是百无聊赖的去各个博物馆闲逛,反而对于当代艺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对色彩明艳的感知,对抽象和具体的平衡,对构图和遐想的感悟。有的时候艺术需要一点空间感,很多作品没有足够的空间是难以诠释它的魅力的。
我觉得凯恩斯投身经济学多少有点是被当时的时事早就出来的——一战、二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们的不安和焦虑产生了对偶像式的经济学家的诉求。如果他完全生长在一个和平年代,那么搞不好他会成长为哲学家而不是注重在某一个具体领域吧。
他当年对经济学的评价至今品来还是蛮有意思:
(经济学)是一种很容易的学科,但很少有人能够表现优异。
这个悖论的解释在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是多种天资的组合...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必须同艺术家那样既超然又不被人收买,但有时又如同政治家那样离现实世界非常近。
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感慨万千的。以前学的学经济学很累,主要是发现对于知识的需求是一个指数增长过程——学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越多、相关的知识越多,于是越发有压力去涉足更多的相关领域。而今读起来,凯恩斯作为一个如此聪明的大脑,当年在经济学还未如此扩张的情况下,便已经感慨出来这里面类似“玄学”的味道——我这里用玄学其实是中性(至少不带贬义)的,因为这个系统实在是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其的认知太有限。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当年还是后面的卢卡斯,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解都有很深刻的一点——这个系统本身是一直在变化的。每当我们对于(处于相对静态的)系统的运转规律更了解一点并加以干涉的时候,系统本身就变了,然后以前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就不准了。这是一个互动和动态博弈的过程,人们只能一点点的沿着自己的足迹去认知这个系统的下一个可能的阶段,而无法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鸟瞰整个局面各种可能的变化。每当我们有一点点发现,然后这个世界又变了,这是一种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可怕却又让人兴奋的状态。真的,很多问题到最后抽象出来都是哲学问题了,因为大家实在是困惑难解。凯恩斯在伊顿公学和剑桥(信使会)都受到了相当密集的哲学训练。我虽然不是特别理解在一个人未经世事(处于象牙塔中)的时候如何可以去感悟哲学的深刻,但或许不同的大脑就是不同的吧,有些思维先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用生动的事实来充实也不错。
还有一段二战前后、马克思主义大为兴盛的时期,凯恩斯对于《资本论》的评价也蛮好玩。背景自然是大萧条、二战的可能阴云下,人们对于前途道路的迷茫的探索。无论是希特勒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探索,还是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都给予了绝望的人群一点希望的光芒。总有人们是相信只有彻底的不同的改变才是改变,而正如凯恩斯所评价的,“俄国是一个难得的拿整个社会做实验”的例子,生在这样的时代也不免让人兴奋。
凯恩斯将《资本论》和《古兰经》相对比,也是蛮有趣的一番相较。“我不明白为何这两本书都能是世界上的一半人口为它们而战?它让我困惑。”说起来倒是给予了当年的《资本论》一个很独特的位置。读《凯恩斯传》,从他父母的结合、到他的出生、上学、工作,一步一步,我一直最大的感慨就是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同样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英伦大地上的思维勃发,欧洲大陆人们也开始对于未来有着不同的认知。在没有一个认知的体系可以主导的年代,百家齐放的想法确实有意思的很。而其实“信仰”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以前洗脑的结果就是对信仰是一味的排斥(虽说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洗脑就是对信仰盲目的跟从)。突然想起,凯恩斯说到信仰也是蛮好玩的,大意为“我们这代人毁灭了新一代的信仰,所以他们是不幸的;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幸接触了这些信仰并毁灭了他们,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这又有点像昨日说到的实用主义了——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实际中可以被检验(证实或者证否)的道理,而最好的检验的便是战乱的年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波折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搬到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最大的感慨就是美国实在是太安逸了——太稳定了。硅谷算是一个创新的区域吧,但是你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无非是简简单单的节奏。看美国大选,最热的依旧是经久不衰的移民、种族、医保等等。这个社会稳定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大家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与压力,而不同于主流派别的学说也就难以发出足够的声音(话说早些时间的AEA居然有个heterodox专场,也是有趣)。
说来,这也跟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既然没办法“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那么面对实际的挑战,我应该如何找寻一条相对安静的道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想象的空间可以很宽广。我一时大概是不会有什么答案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体会波折之中的兴奋与灵感,注意到一些以前未曾注意或者懒得注意的生活侧面,然后给自己一些更加新鲜的启迪与想法。
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读完,大概还有个几十页。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写下(三),可能有些想法,可能也没有什么想法。不过还是蛮喜欢这种毫无功利心的读书的状态——我也不知道自己想看的是什么,那就随便看看随便记记,灵感也不是说来就来的,还是有一些积淀才能共鸣吧。